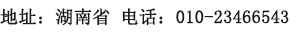那一瞬间,我爹说他将手里的汽灯甩出去,那只追击他的秦岭山中最凶猛的野兽——金钱豹随光扑下了悬崖。一碗水,缓上气来才对围着他的工友说,“金…钱....豹……连汽灯摔下石嘴山。”
“我要扒它的皮当褥子铺!”
“喝它的血,补身子!”
“吃豹子肉,壮胆!”
“走!”
地处秦岭石嘴山,林深、路悬且黑,他们的豹皮褥子、喝豹血、吃豹子肉迅猛行动今夜取消。
我趴在还在宝鸡市长寿中学上初一的小姑背上,看到那个戴着已经洗得发白的**帽穿着黑尼大衣的父亲和他的战友**局长许伯伯一下吉普车就上了篮球场。
我婆说,她赶过鸡凤山的庙会。“耶,那秦岭上的长虫像桶么粗的。就是石嘴山下那棵牛头青槐树底下泉水,长虫从山上溜套“噬”地一声溜下来喝水,碰上茄娃担水。把莫大个人给吃咧。等人知道,只剩下血糊糊地一对扁担上的铁勾搭。”
我爷说,“后头这长虫就吃老山里人的猪、牛、羊。茄娃他爹是杀猪的,就在那条长虫下山的溜套里倒插了七把杀猪刀。正晌午,那长虫叱地下来,肚子划开七道又大又长又深的血口子;疼得那厮跳起来尾巴扫飞了茄娃家的草房,不见了半个山……”
我急问:“茄娃他爸哩?”
“死了。”
“咋死的?”
“山里人有牛脾气,让山山岭岭的人吃了半个月横死在石嘴山边的长虫肉。又是搭棚又是盖房,可没过几年好日子。金钱豹来了……”
“啊?”我想起了父亲的遇险。
“金钱豹,满身是麻麻钱。凶得很,吃猪吃羊。茄娃他爸,大难不死,成了山里人的英雄。他拉了只猪娃,在山脊梁挖了个深坑,里头放了个设有机关的大木箱,棚上树梢。半夜里他藏在木箱背后捏着猪娃吱吱喽喽地叫唤。那只金钱豹远远地听见,冲上山梁子猛钻了进去。猪娃吃不得,又被木箱“咔嚓”套住。那急迫中的困兽喧天地吼叫,蹦碎了木箱,挖破他的嘴脸,肠子淌了一地……”
“那人?”我听到这惨景,心里十分害怕。“那人死了吗?”
“死了。那么凶险的场面,他能活吗?”
惊愕之余,我回到了下房。
父亲给我和小姑说,“第二天,我去量了一下那晚跑出的步子,一步足足三公尺……”
“是三米吗?”小姑问。
父亲回答:“三米。”
“耶。”小姑吐着舌头。
父亲说道:“其实,光听山里人说金钱豹怎么怎么厉害,我们修宝成铁路的人谁都没见过。那天,有个哑炮没响。我下山晚,天黑走到半山腰石嘴山牛头泉,听着像是汴哒汴哒水响,把手里的汽灯抬高一亮,那两只眼睛像两柱手电筒的强光射来。那家伙一惊磕立倒腾奔上山顶,听着一声震天欲裂的吼叫,又猛扑了下来。我惊慌地往山下跑。人的速度哪能和野兽比?我跑着,只觉着腿短只路长,那只利爪挖到我的脊梁骨……悬崖拐弯处跑得太快摔出汽灯抱住了树……”
“豹子上了爹的当,摔死了?”
“没有。”
“我们第二天赶到河底,只见到那里有一滩血,一滴一滴进了南山。”
听到这里,我很是遗憾。
父亲把指挥部那个大贪污犯送上法庭,枪毙了。
秋季,父亲没坐他的吉普车,依然戴着他那顶洗得发白的*帽回来了。他煞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
父亲回来的三天里我家发生了三件大事:
天,村里贴出白纸黑字布告;我家是漏划地主。
第二天,我爷得绞肠痧死了。
第三天,父亲悬梁自尽。
Tie:
.5.11晚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